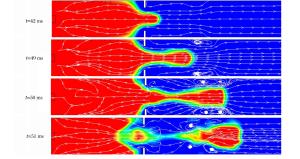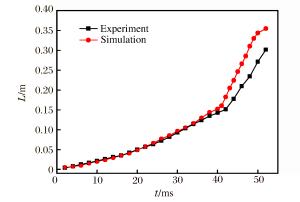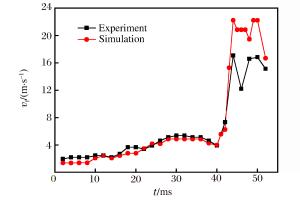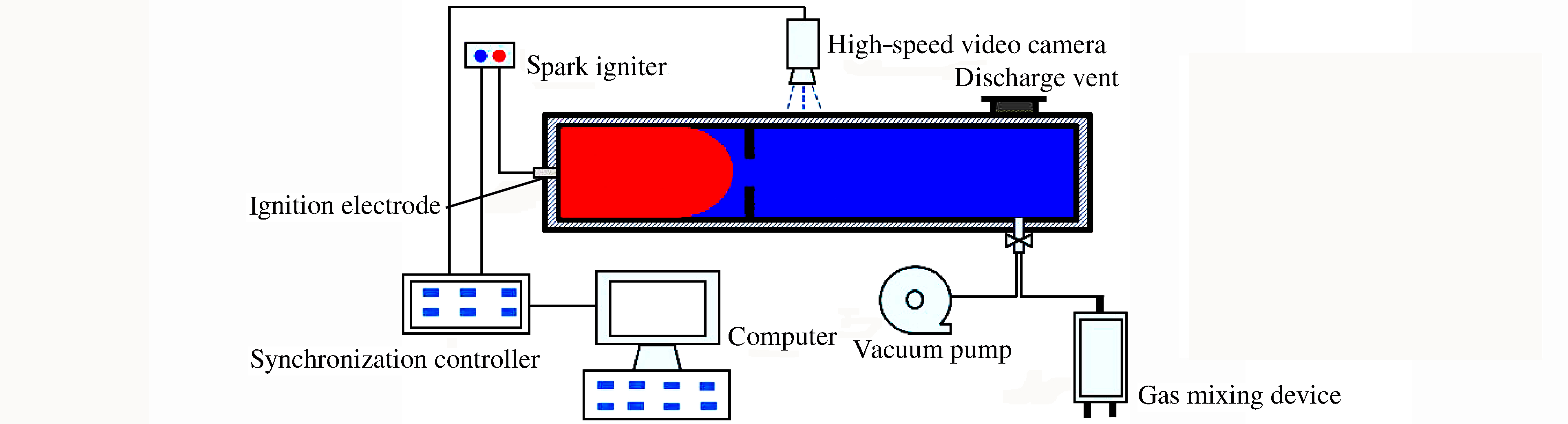| [1] |
Dorofeev S B. Flame acceleration and explosion safety applications[J]. Proceedings of the Combustion Institute, 2011, 33(2):2161-2175. doi: 10.1016/j.proci.2010.09.008
|
| [2] |
Alharbi A, Masri A R, Ibrahim S S. Turbulent premixed flames of CNG, LPG, and H2 propagating past repeated obstacles[J]. Experimental Thermal and Fluid Science, 2014, 56(7):2-8. http://www.wanfangdata.com.cn/details/detail.do?_type=perio&id=cab80255e3dd2ac1e24881d2a44ea68e
|
| [3] |
Johansen C T, Ciccarelli G. Modeling the initial flame acceleration in an obstructed channel using large eddy simulation[J]. Journal of Loss Prevention in the Process Industries, 2013, 26(4):571-585. doi: 10.1016/j.jlp.2012.12.005
|
| [4] |
陈志华, 叶经方, 范宝春, 等.方形管内楔形障碍物对火焰结构与传播的影响[J]. 爆炸与冲击, 2006, 26(3):208-213. doi: 10.3321/j.issn:1001-1455.2006.03.003Chen Zhihua, Ye Jingfang, Fan Baochun, et al. Effects of a wedge obstacle on flame propagation and its structure[J]. Explosion and Shock Waves, 2006, 26(3):208-213. doi: 10.3321/j.issn:1001-1455.2006.03.003
|
| [5] |
Ciccarelli G, Dorofeev S. Flame acceleration and transition to detonation in ducts[J]. Progress in Energy & Combustion Science, 2008, 34(4):499-550. http://www.wanfangdata.com.cn/details/detail.do?_type=perio&id=718edb9b92782b6bc9b5758162d9bbdb
|
| [6] |
Kundu S, Zanganeh J, Moghtaderi B. A review on understanding explosions from methane-air mixture[J]. Journal of Loss Prevention in the Process Industries, 2016(40):507-523. http://www.wanfangdata.com.cn/details/detail.do?_type=perio&id=bd0c31f6cbd2e040995370fc181d2079
|
| [7] |
Masri A R, Ibrahim S S, Nehzat N, et al. Experimental study of premixed flame propagation over various solid obstructions[J]. Experimental Thermal and Fluid Science, 2000, 21(1/2/3):109-116. http://www.wanfangdata.com.cn/details/detail.do?_type=perio&id=ff5b56c451e0a34d392f7a4e791e637b
|
| [8] |
Hall R, Masri A R, Yaroshchyk P, et al. Effects of position and frequency of obstacles on turbulent premixed propagating flames[J]. Combustion and Flame, 2009, 156(2):439-446. doi: 10.1016/j.combustflame.2008.08.002
|
| [9] |
Chen P, Li Y C, Huang F J, et al. Experimental and LES investigation of premixed methane/air flame propagating in a chamber for three obstacle BR configurations[J]. Journal of Loss Prevention in the Process Industries, 2016, 41(5):48-54. http://www.wanfangdata.com.cn/details/detail.do?_type=perio&id=a21f326d49cd196d10940be6b2b2ce86
|
| [10] |
Wen X P, Yu M G, Liu Z C, et al. Large eddy simulation of methane-air deflagration in an obstructed chamber using different combustion models[J]. Journal of Loss Prevention in the Process Industries, 2012, 25(25):730-738. http://www.wanfangdata.com.cn/details/detail.do?_type=perio&id=01e1b3eb9b77325460e27f3d572d02aa
|
| [11] |
Johansen C T, Ciccarelli G. Visualization of the unburned gas flow field ahead of an accelerating flame in an obstructed square channel[J]. Combustion and Flame, 2009, 156(2):405-416. doi: 10.1016/j.combustflame.2008.07.010
|
| [12] |
Sarli V D, Benedetto A D, Russo G, et al. Large eddy simulation and PIV measurements of unsteady flames accelerated by obstacles[J]. Flow Turbulence and Combustion, 2009, 83(2):227-250. doi: 10.1007/s10494-008-9198-3
|
| [13] |
Sarli V D, Benedetto A D, Russo G. Sub-grid scale combustion models for large eddy simulation of unsteady premixed flame propagation around obstacles[J].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, 2010, 180(1/2/3):71-78. http://www.wanfangdata.com.cn/details/detail.do?_type=perio&id=8e2c1f3fb6857178dce5a963fa5e1fac
|
| [14] |
Ibrahim S S, Gubba S R, Malalasekera W, et al. Calculations of explosion deflagration flames using a dynamic flame surface density model[J]. Combustion, Explosion, and Shock Waves, 2012, 48(4):393-405. doi: 10.1134/S0010508212040041
|
| [15] |
马秋菊, 张奇, 庞磊.巷道壁面与瓦斯爆炸相互作用的数值模拟[J]. 爆炸与冲击, 2014, 34(1):23-27. doi: 10.3969/j.issn.1001-1455.2014.01.005Ma Qiuju, Zhang Qi, Pang Lei.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interaction between laneway surface and methane explosion[J]. Explosion and Shock Waves, 2014, 34(1):23-27. doi: 10.3969/j.issn.1001-1455.2014.01.005
|
| [16] |
Gubba S R, Ibrahim S S, Malalasekera W, et al. Measurements and LES calculations of turbulent premixed flame propagation past repeated obstacles[J]. Combustion and Flame, 2011, 158(12):2465-2481. doi: 10.1016/j.combustflame.2011.05.008
|
| [17] |
Zimont V L, Battaglia V. Joint RANS/LES approach to premixed flame modell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TFC combustion model[J]. Flow Turbulence and Combustion, 2006, 77(1):305-331. http://www.wanfangdata.com.cn/details/detail.do?_type=perio&id=dc0a05d36d25fa51a6a6e96a1f6b0ad9
|







 下载:
下载: